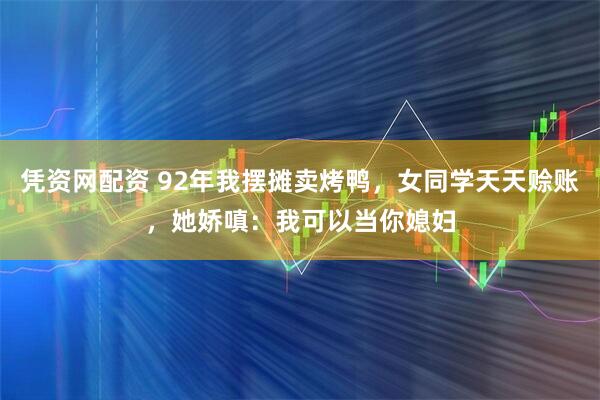
一九九二年的风,吹过县城老槐树的叶子,也吹过我那辆吱呀作响的三轮车。车斗里,是我全部的家当和指望——一个改造过的铁皮桶烤炉,一筐从乡下收来的肥嫩鸭子,还有祖传下来的一手烤鸭手艺。
我叫刘大福,人如其名,爹妈就盼着我这辈子能有大福气。可惜,福气还没影儿,生活的担子倒是先实实在在地压在了刚二十出头的肩膀上。爹走得早,娘身体不好,家里还有个正在念高中的妹妹,我这当大哥的,读完高中就理所当然地撂下了书包,继承了这祖传的烤鸭摊子。
我的摊位,固定在南街的拐角,一棵大槐树下,旁边是王婶的杂货铺和赵叔的修鞋摊。每天下午三点出摊,那烤炉一生起来,混合了果木清甜和鸭油焦香的独特气味,就能勾得半条街的人食指大动。橙红色的鸭皮油光锃亮,用牛皮纸一包,还烫手呢,咬下去那一声“咔嚓”脆响,紧接着是丰腴肉汁在口腔里迸射,是我刘大福最自豪的招牌。
生活就像我那烤炉里的火,不温不火,按部就班。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一天天过去,直到攒够钱,翻修一下家里的老房子,或许再经人介绍,娶个踏实姑娘,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
直到那天,李丽华出现了。
展开剩余91%那是一个霞光满天的傍晚,收摊的、下班的,街上人来人往。我正在给一位熟客片鸭子,眼角余光瞥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站在了摊子前,带着几分犹豫和局促。
“同……同学,你这烤鸭,怎么卖?”
声音清清脆脆的,像夏天井水里镇过的黄瓜。我抬起头,愣住了。
站在我面前的,是李丽华。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,那个坐在前排,总是扎着马尾辫,笑起来眼睛像月牙儿一样的姑娘。她比上学时更清秀了,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,脸庞在夕阳余晖里透着细腻的光泽,只是眉宇间,似乎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愁容。
“李……李丽华?”我有些不敢相信。高中毕业后,同学们各奔东西,她成绩好,听说去念了师范,怎么会在这里?
她脸上飞起一抹红晕,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:“刘大福,真是你啊。我刚才远远看着就像,没敢认。”她的目光落在我围裙上的油渍,又看了看我手里的烤鸭刀,眼神里没有鄙夷,只有一种恍然的确认。
“是我。”我憨厚地笑了笑,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手,“老同学,好久不见。这烤鸭,论只卖十八,半只九块五,也可以单买片好的鸭肉或者鸭架。”
“十八块……”她小声重复了一下,手指下意识地捏紧了手里那个有些旧的花布口袋,脸上掠过一丝为难。
我心里明白了七八分。老同学见面,本该高兴,可她这神情,不像是来叙旧,倒像是被这价钱难住了。我记得她家境似乎也不太好,母亲身体一直不好,父亲只是个普通工人。
“那个……我今天没带够钱,”她声音更低了,带着恳求,“能不能……先赊着?我买半只,给我妈尝尝,她最近胃口不好,就想吃点有滋味的东西。”她抬起头,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,“我过两天一定给你送来!”
那一刻,她眼里的孝心和那份小心翼翼的窘迫,像一根柔软的羽毛,轻轻搔了一下我的心尖。我没怎么犹豫,拿起油光纸,利落地包了半只烤得最好的鸭子,又额外加了一只肥嫩的鸭腿,塞到她手里。
“拿着,老同学了,说什么赊不赊的。这半只鸭子,算我请阿姨吃的。”
“那不行!”她急忙摆手,“钱一定要给的!说赊就是赊,我肯定还你!”
看她坚持,我只好点点头:“成,那你方便的时候再说。代我问阿姨好。”
她接过烤鸭,连声道谢,脸上绽放出感激又带着点羞怯的笑容,像一阵清凉的风,吹散了我摊位上空的油烟燥热。她转身走了,碎花裙摆消失在熙攘的人群里,我那颗被炉火烤得有些麻木的心,却莫名地跳快了几拍。
我以为这只是个插曲。没想到,两天后,李丽华又来了。
依旧是傍晚时分,她脸上带着点奔跑后的红晕,从那个花布口袋里,小心翼翼地数出九块五毛钱,整整齐齐地放在我的钱盒里。
“刘大福,谢谢你啊,我妈说你的烤鸭特别香,她吃了小半只呢,胃口都好多了。”她笑着说,眼睛弯成了好看的月牙。
我心里为她高兴,顺口问了一句:“阿姨身体好些了就好。你这是……在哪儿上班呢?”
她眼神黯淡了一下:“我没念完师范,家里……情况不太好,我就回来了。现在在街道的绣花厂做临时工,计件的,活儿不多。”
我“哦”了一声,不知该说什么安慰她。生活的艰难,我感同身受。
从那以后,李丽华就成了我摊子上的常客。不,不能算常客,因为她很少当场付钱。她总是隔三差五地来,有时候买四分之一只,有时候只买一个鸭架,或者一小份片鸭肉,每一次,都带着那种让我无法拒绝的、混合着歉意和期盼的眼神,轻声问:“大福,能再赊给我吗?发了工钱就还你。”
我的记账本上,属于“李丽华”的那一页,赊欠的金额画了好几个“正”字。王婶和赵叔有时候会打趣我:“大福,你那漂亮女同学,不会是看上你这烤鸭了吧?这账赊得,都快成股东了。”
我只是嘿嘿傻笑,不接话。心里却像揣了只兔子,她每次来,我都莫名地有些紧张,又有些期待。我会特意把烤得最均匀、皮色最漂亮的部位留给她,会在包鸭子的时候,偷偷多塞几块鸭肉或者一个鸭胗。她似乎察觉了,每次接过时,都会飞快地看我一眼,那眼神里除了感激,似乎还有些别的东西,让我的脸皮微微发烫。
我知道她赊账不是为了自己。她每次来,十有八九都是说“我妈想吃点好的”、“给我爸下酒”、“给弟弟解解馋”。她的孝顺和善良,像她的人一样,干干净净,温润如玉。
有一天,雨下得很大,街上没什么人。我撑着大伞守着摊子,以为她不会来了。却看见她撑着一把破旧的油纸伞,裤脚湿了大半,深一脚浅一脚地跑过来。
“还好你没收摊!”她喘着气,额前的刘海湿漉漉地贴在皮肤上,“我妈今天生日,非要吃你家的烤鸭,说别家的没这个味儿。”
我心里一热,赶紧给她包了整整一只鸭子,又拌了一份爽口的黄瓜丝。“快拿回去,别让阿姨等急了。钱不着急。”
她看着那只肥硕的烤鸭,犹豫了一下:“这……一只太多了……”
“不多不多,生日嘛,热闹!”我打断她,“快回去吧,路滑。”
她看着我,雨水打湿的眼睫毛长长的,眼睛像被水洗过的黑葡萄。她没再说谢谢,只是轻轻点了点头,抱着烤鸭,又冲进了雨幕里。那一刻,我看着她的背影,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:要是能天天给她烤鸭子吃,该多好。
这个念头把我自己吓了一跳,赶紧摇摇头,往炉子里添了块柴火。刘大福啊刘大福,你一个卖烤鸭的,瞎想什么呢。
日子就在这烤鸭的香气和她的赊账中,不紧不慢地流淌。我们的关系,也在这赊赊欠欠中,悄然发生着变化。她不再只是站在摊子前赊账,偶尔来得早,我还没收摊,她会帮我递一下牛皮纸,或者在我忙得腾不开手时,帮客人找找零钱。她会跟我聊她绣花厂里的趣事,聊她母亲的病情,聊她弟弟的学业。我也会跟她抱怨一下今天收的鸭子不够肥,或者炉火总是不太旺。
我们之间,那种老同学的生分渐渐褪去,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亲近和默契。
转折发生在一个夏末的夜晚。那天生意特别好,烤鸭早早卖完了。我收拾完摊子,骑着空三轮车往回走。路过人民公园门口时,却看见李丽华一个人坐在石凳上,肩膀微微抽动,像是在哭。
我心里一紧,赶紧停下车走过去。
“丽华?你怎么了?”
她抬起头,脸上果然挂着泪痕,看到是我,慌忙用手背去擦。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
“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?”我在她旁边坐下,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
她摇摇头,沉默了一会儿,才低声说:“是我妈……今天去医院复查,医生说情况不太好,要住院,要用一种很贵的药……我爹厂里效益也不好,都快发不出工资了……”她说着,眼泪又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掉下来,“我心里难受,又不敢在家里哭,怕他们担心……”
月光洒在她苍白的脸上,泪珠晶莹。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,又酸又疼。我想拍拍她的背,又觉得唐突,手抬起来,最终只是笨拙地递过去我那块擦汗的毛巾——虽然也不算太干净。
“别哭,别哭,”我搜肠刮肚地想安慰她,“阿姨吉人天相,会好起来的。钱……钱的事,总会有办法的。”
“能有什么办法?”她哽咽着,“我那份临时工,挣的钱也就刚够吃饭。大福,我不怕吃苦,我就是……就是看着我妈那样,我心里难受……”她抬起泪眼望着我,“这些日子,多亏了你。要不是能赊点烤鸭给我妈改善伙食,我心里更过意不去。欠你的钱,我……”
“快别这么说!”我急忙打断她,“那点钱算什么!咱们是同学,互相帮衬不是应该的吗?以后你想给阿姨吃什么,尽管来拿,不许再提钱的事!”
她看着我,眼睛水汪汪的,里面映着月光,也映着我有些焦急的脸。忽然,她轻轻靠在了我的肩膀上。
我浑身一僵,血液仿佛瞬间冲上了头顶,整个人都呆住了。她的头发带着淡淡的皂角清香,混着泪水微凉的气息,萦绕在我的鼻尖。我能感觉到她单薄肩膀的微微颤动。过了好几秒,我才像被解了穴道一样,小心翼翼地,用手臂轻轻环住了她的肩膀。
那一刻,公园里的蝉鸣,远处马路上的车声,仿佛都消失了。世界里只剩下她低低的啜泣声,和我如擂鼓般的心跳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她慢慢止住了哭泣,有些不好意思地直起身子,脸颊绯红。“对不起啊,把你衣服弄湿了。”
“没、没事。”我喉咙发干,心跳依旧快得不像话。
我们并肩坐着,一时无言,气氛有些微妙的尴尬,又充满了某种甜腻的暖昧。
忽然,她像是想起了什么,转过头看着我,眼睛还红红的,却故意做出一种娇嗔的表情,声音又轻又软,带着点撒娇的意味:
“刘大福,我这么天天赊账,你是不是都快烦死我了?”
“哪有!绝对没有!”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。
她抿嘴笑了笑,眼睛弯弯的,像只狡黠的小狐狸,然后凑近了一些,吐气如兰,用那种让我心跳瞬间漏拍的语气说:
“那……你看这样行不行?我……我可以当你媳妇……这样能不能免费吃一辈子烤鸭?”
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。
我瞪大了眼睛,看着她近在咫尺的、带着泪痕却又笑得俏皮的脸,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炉火烤得出现了幻听。血液轰的一声全都涌向了大脑,耳朵里嗡嗡作响。
“你……你说啥?”我的声音干涩得厉害。
她的脸更红了,连耳垂都染上了胭脂色,但却没有躲闪我的目光,反而勇敢地重复了一遍,声音虽轻,却异常清晰:“我说,我给你当媳妇,是不是就能一辈子免费吃你的烤鸭了?”
巨大的、难以置信的狂喜,像夏日暴涨的河水,瞬间冲垮了我所有的理智和拘谨。我猛地站起来,因为动作太猛,差点带翻了石凳。我抓住她的手,她的手很软,微微有些凉。
“能!太能了!”我激动得语无伦次,声音都在发抖,“不止一辈子!下辈子,下下辈子都行!丽华,你……你说的是真的?你不是在开玩笑吧?我……我就是个卖烤鸭的,我……”
她看着我手足无措的样子,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,用力抽回手,嗔怪地打了我一下:“傻样儿!谁跟你开玩笑!卖烤鸭的怎么了?你手艺好,人实在,心地善良,比什么都强!”
她顿了顿,脸上带着少女的羞涩和坚定:“其实……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就……就有点喜欢你了。你老实巴交的,打球输了也不急眼,还会偷偷帮值日生打扫卫生……只是那会儿光知道学习,没敢往那方面想。后来回来,在街上看到你卖烤鸭,那么认真,那么踏实,我就……反正,我觉得你就是我要找的人!”
原来,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。原来,那些偷偷多给的鸭肉,那些故作镇定的关心,她都懂。原来,她和我一样,早就埋下了种子,只等一个时机,破土而出。
那一晚,我几乎是飘着回家的。三轮车蹬得飞快,夏夜的风吹在脸上,都是甜的。天上的星星好像特别亮,路上的行人好像都在对我笑。我刘大福,何德何能,能拥有这么好的姑娘的青睐!
从那以后,一切都不同了。
李丽华还是经常来我的摊子,但不再是“赊账”,而是名正言顺地来“帮忙”。她手脚麻利,嘴又甜,帮着招呼客人,收钱算账,比我还在行。王婶和赵叔看着我们,笑得合不拢嘴,直说“大福这小子,傻人有傻福”。
我们开始正式谈恋爱。像所有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,含蓄又热烈。收摊后,我会用三轮车载着她,在县城并不宽阔的马路上慢慢骑。我们会一起去河边散步,她跟我讲绣花的花样,我跟她讲挑选鸭子的门道。她母亲住院,我每天雷打不动地送一碗用鸭架熬的汤,汤里总会藏着几块最嫩的鸭肉。她父亲和弟弟,也吃惯了我家的烤鸭。
拮据依然是生活的底色,但因为有了一起面对的人,苦涩里便长出了希望的甜。
那年中秋,我提了四只最肥的烤鸭,两瓶好酒,鼓足勇气去了她家。她父亲,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,接过烤鸭,拍了拍我的肩膀,说了句:“丽华跟着你,我放心。”她母亲靠在床上,气色比之前好了些,拉着我的手,一个劲地说:“大福是好孩子,丽华交给你,我安心。”
我的眼眶瞬间就湿了。这就是认可,是托付。
从她家出来,月光如水银泻地。我和丽华手牵着手,走在安静的巷子里。
“大福,”她轻声叫我,“等明年,我绣花厂要是能转正,收入稳定点,咱们就……就把事办了吧。”
我紧紧握住她的手,心里被巨大的幸福和责任感填满。“嗯!你放心,丽华,我以后一定更努力,多挣钱,让你和叔叔阿姨都过上好日子!我要把烤鸭摊扩大,说不定以后还能开个店,就叫‘福记烤鸭’!”
她靠在我肩膀上,咯咯地笑:“好呀,那我就是老板娘,专门负责收钱!”
我们相视而笑,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。
年底的时候,我用攒下的钱,给她买了一条红色的羊毛围巾。她戴上,衬得小脸愈发白皙娇俏。她则用攒下的工钱,给我织了一双手套,厚厚的,说是冬天出摊戴着,手就不冷了。
一九九二年的冬天,似乎格外的暖和。
如今,三十年过去了。我的“福记烤鸭”真的开了起来,还不止一家。当年的三轮车和铁皮桶烤炉,早已进了仓库留作纪念。店里用的是现代化的电烤炉,稳定,高效。但有时候,我还会在后院用果木生起一堆火,给自己家人烤一只,那才是记忆里的味道。
李丽华,我的丽华,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为半只烤鸭赊账的羞涩姑娘了。她是“福记烤鸭”的老板娘,是能干的当家主母,是我两个孩子的妈。岁月待她温柔,只是眼角添了几道细纹,笑起来,眼睛还是像月牙儿。
偶尔,在店里不忙的午后,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,她会走到我身边,像年轻时那样,用胳膊肘轻轻碰碰我,带着那熟悉的、永远能撩动我心弦的娇嗔:
“哎,刘大福,当初要不是我天天去赊账,你这傻小子是不是永远不敢开口?”
我放下手里的账本,看着她眼里的狡黠和笑意,伸手握住她不再细腻却依旧温暖的手,像过去无数个日子一样,憨憨地,却又无比认真地回答:
“是啊,多亏了你赊账。不然我哪骗得到这么好看的媳妇,还免费吃了我一辈子烤鸭。”
她便会心满意足地笑起来,那笑容,一如一九九二年夏天,槐树下,她第一次赊账时,带着羞涩和期盼的模样。
原来,世间最甜蜜的“债”,是赊来的缘分。而最幸福的事,就是用一辈子的时光,去慢慢“偿还”。我的大福气,原来从一开始,就裹着烤鸭的香气,来到了我身边。
发布于:陕西省科元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